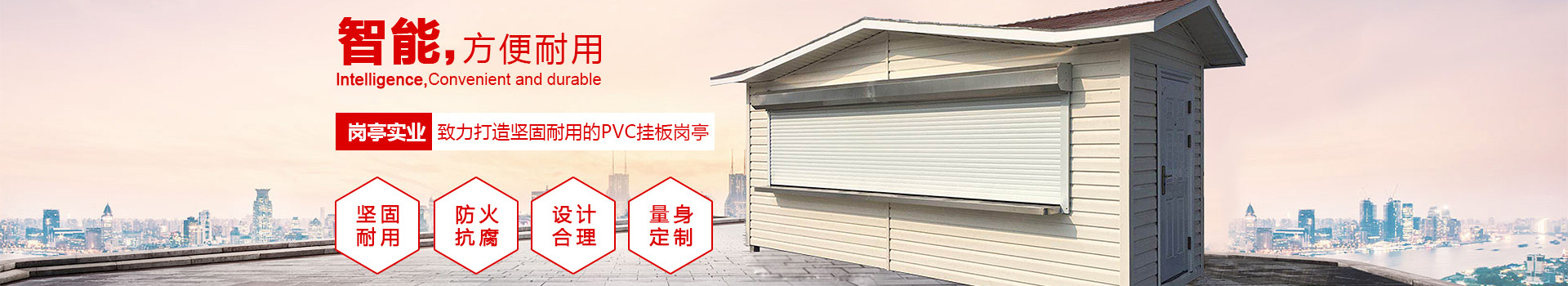波音已经逐渐抽身出这个曾经由它发力创建的赛道:人才流失,对应的是创造力停滞;NASA转型,带走了基本的资金支持和订单保证;拒绝定价合同,与SpaceX理念分道,是在形式上拒绝了商业航天时代的当下范式。
波音的商业载人飞船Starliner大概要迎来首次搭载人类宇航员的发射了。
多次延期、仍在计划中的发射已经比原计划慢了4年,也比竞争对手SpaceX晚了4年。一次次项目延期,让Starliner任务的重要性大幅褪色。除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对波音的依赖逐渐降低,Starliner本身在波音体系里受到的关注也大不如前。
我们看过太多SpaceX的成功往事,小子逆袭的励志和航天成就的恢弘总是易于传唱。以至于很少有人想起,Starliner和波音才是开启了美国商业载人计划的更关键要素。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拿下这个合同算起,十年过去了。这段时间里,美国总统换了两届,NASA负责人也因此轮换数任,SpaceX从野蛮人变成了行业灯塔,商业航天格局转变。而波音,人们更记得的是两架737 MAX飞机因软件问题坠毁,让其陷入深深的泥潭。
波音在Starliner一步一步落后,是一场从指标、成本、内部体制的全方面落败。这个过程也构成了SpaceX故事的B面,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捆绑了官方意志的航天产业,是如何在商业力量参与下被重新塑形。
伟大的技术进步来自于敢于冒险、勇于颠覆的企业家,以及拥有更长远目光的政府支持。商业航天就是这样的叙事。
但在那个SpaceX没有成为一种正确答案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阻力和偶然的过程。波音一度是扫平障碍、开启了商业化尝试的关键角色。
2010年2月1日,奥巴马总统上任不久,治下的美国政府为NASA作出一笔190亿美元的预算案,正式提出了商业载人计划(Commercial Crew Program),与工业界合作,将宇航员运送到空间站。
这是商业载人航天故事的开始,但并非毫无代价。当时更多人更关注预算案的另一个重点,原本剑指火星的载人航天探索项目星座计划(Constellation program)被直接砍掉。
图:2010年4月,奥巴马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宣布了该届政府的太空政策,商业载人计划为重点之一。丨来源:NASA
传统的航天集团在星座计划中捆绑了诸多利益,于是发动大量的游说力量反对这个新总统提出的预算案。当时的多数国会和NASA内部人员疾呼:此举是NASA将载人航天的能力拱手出让。
“总统提出的方案开启了美国载人航天的死亡征程。”负责处理NASA资金的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参议员查德 · 谢尔比说。“这些商业公司甚至不能把垃圾从空间站运回来,更别提把人安全地送上太空。”曾经的美国国家英雄、宇航员吉恩 · 塞尔南(Gene Cernan)在国会作证时指责说:“不仅载人航天和太空探索处于危险之中,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将面临危险。”
现在我们能在当时的证词中感受到,商业载人计划并不是当时的政治正确。而保守且背景强大的官僚体系就是法案的最大阻力。
所以哪怕是在奥巴马的支持下,商业载人项目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收获信任,政府要员、国家英雄在国会面前高调反对,让国会死死地卡住了新总统的预算案。
直到波音站出来,表示愿意支持项目,以巨头之姿参与其中。交战双方迅速找到了各自都能接受的公约数,对反对者来说,波音至少是一个可靠的老朋友。对支持太空进一步商业化的一方来说,就算不喜欢波音,项目能够推进就是最重要一步。
预算到位,一次重要会议在华盛顿特区的NASA总部举行,核心要义是分钱。几十年来领导开发了航天飞机、监督国际空间站建设的NASA官员凑到一起,要讨论谁来拿到这笔热钱。而直到这个时候,SpaceX还是一个陪跑的角色。
会议的氛围像是在走过场,波音是最自然的选择,房间里的多数人认为,商业载人飞船的合同不管是十亿还是百亿,直接让波音过来签就好。直到会议接近尾声,才有声音提出可以纳入另一家公司作为竞争者,于是SpaceX作为备胎被搬上了会议桌,像一个无关痛痒的龙套演员,被挂在会议的结尾。
几个月后,NASA公布了最终选择:商业载人飞船的合同花开两朵:42亿美元给波音,26亿美元给SpaceX。前者拿走三分之二的资金,但还是认为输了一场比赛,波音的不满基于一个预设:没有波音就没有这个预算案,他们为了拿到全部的资金极力游说,但最后还是被SpaceX“偷走”了一部分。
故事在这里才正式开始,从这个角度看,SpaceX是被波音带着进入赛场。而且,波音充满信心,在后续的开发工作中轻松击败SpaceX。
后来我们知道,从那份合同算起的十年,是所有人看着SpaceX新王登基的十年。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SpaceX在拿下载人项目合同的同一时间,几个重大项目都在同步进行:更新猎鹰9号火箭、提高发射频率、测试着陆器以及执行空间站送货任务。新的合同带来了钱,也塞进来更多工作,但SpaceX的团队还是那么些。SpaceX需要从零开始挑战这个仅有4个国家完成过、被称为皇冠的项目。
一位曾与SpaceX和波音密切交流的NASA工程师走进SpaceX,看到内部的气氛就像是一个疯狂的研究生院,不同项目的压力分配在同一个团队上,根本不可能专注于一个任务,载人飞船项目就这样被混乱地推动向前。
但至少SpaceX仍处在自己熟悉且擅长的气氛里。而波音的太空部门则需要适应新的逻辑,改掉以往的肌肉记忆。
波音的太空部门很知道飞船怎么造,但他们从未执行过定价合同。在此之前,波音从领导层到工程师,前半辈子都在“成本+”(Cost-Plus)的环境中成长,即政府报销了成本中的每一分钱,再付一笔可以计入盈利的费用。这不只是钱的问题,而是在那个模式里,成本超支和任务延误的后果都可以让NASA来承担。波音永远在赢。
艰难回归商业逻辑的过程中,Starliner项目上每多投入一分钱,都意味着利润同步减少一分钱,结果是Starliner项目在波音庞大的内部体系中获得的资源远远不够。
“两家公司的文化、设计理念和决策流程之间的差异,让SpaceX在定价合同的竞赛里一马当先。波音抱着大量的资金,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洛里·加弗(Lori Garver)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是前NASA副局长,曾是奥巴马总统的太空政策顾问、预算案的重要推手。
带着过去的动作惯性,波音在软件系统的开发上,一头扎进了难以逆转的技术泥潭里。不像SpaceX一个团队兼顾多个项目,在波音,一个项目连带着相关的责任被分散给了不同的团队,以至于他们没有统一的飞行软件团队。
其中一个团队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负责地面阶段的软件运行;而到了发射前最后几分钟,另一个位于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的团队就会接手,负责管理起飞时及后续的软件运行。
可怕的是,这两个并肩的团队不仅没有信任,还互相嫌弃。Arstechnica的航天记者艾瑞克·伯格(Eric Berger)就在采访中发现,在多数时间里,他们分居两地,独立运作,松散地拼凑这个即将受挫的飞船项目。
深植于体系内的裂痕,隐蔽而致命。最终在2019年12月的首次试飞任务里,Starliner顶着所有人的目光点火升空,迎来了第一个清算时刻。
问题在火箭升空后立即出现。最致命的错误是最低级的,飞船上的时钟没有和地面进行同步,两者相差了11小时。飞行过程中,飞船根据错误的时间进行计算,认为飞船偏离了轨道,于是启动发动机试图矫正,很快就把相当有限的燃料耗尽,空间站之旅提前结束。
“灾难性的失败”,NASA高级官员用这个词来形容这次任务。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低级的错误让飞船“死”在了半路,而不是发生在和空间站的对接阶段,避免了把空间站一并带走的终极悲剧。
图:Starliner首次测试现场,左一为佛州州长,右一为NASA局长吉姆 · 布里登斯汀,他在发射一个小时后宣布任务失败。丨来源:NASA
几个月后,波音在这个项目上的最高负责人在记者面前承认:波音从未对软件进行端对端的全过程测试,只进行了分阶段测试。这种低级问题很容易在端到端测试中被发现。
按照美好的计划,那次发射是Starliner进行正式载人任务前的最后一步测试,波音会在次年(2020)比SpaceX更早一步把宇航员送上空间站。然而一步失败,让波音眼睁睁看着SpaceX率先完成测试、完成正式的载人航天任务,成为唯一能够执行载人任务的航天公司。
直到如今2024年5月,波音还没走完这一步,以高昂的代价输掉了这场比赛。4年前,SpaceX载人龙飞船首次将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至今已经完成13次正式任务,持续为公司挣钱。而由于飞船开发的延误,波音在Starliner上已经超支超过15亿美元,这个数字不仅还在持续上升,也会一分不少地计入波音的亏损当中。
连带被打脸的是NASA。很多人开始指责他们,作为波音的“干爹”,在钦点波音拿下合同后却没有进行应有的监督。相较于SpaceX,波音是NASA眼里绝对优秀的选手,信任让NASA放松了要求。
任务失败是一个缺口,波音内部的烂账,以及和供应商之间的离谱矛盾也在事件后被悉数挖出。
波音拿下合同后就找来了洛克达因,把Starliner发动机分包给他们的同时,也把后者视为好兄弟,一起完成商业航天的大事业,言下之意是:好兄弟不能太计较钱。而洛克达因则认为自己只是承包商,还是按照以前的惯例,收多少钱办多少事。
隔阂在项目早期就出现了。波音要求洛克达因调整零部件的规格,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业务沟通,而后者的态度是:增加了工作量,就要加钱。波音因此被突然激怒。
在那之后,双方团队关系剑拔弩张,实际工作中也鲜有合作迭代的动作。2018年6月,Starliner在一处NASA的场地内进行发射中止系统测试,飞行器成功点火,但由于设计问题,点火终止时8个推进剂阀门中有4个失灵。超过1.8吨毒性推进剂甲基肼倾泄在测试台上,巨大的火球吞噬了周围属于NASA的地面设备。
“波音公司和洛克达因互相憎恨,”一位参与测试的人在今年匿名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实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每个人已经处于超级防御模式。这已经被定位为风险因素,但双方并没有开诚布公地讨论和解决。”归因时,两家公司沟通不畅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
公司之间的拉扯从未停下。在2021年下半年,Starliner因为推进系统中的粘性阀门出现故障,飞船的第二次无人试飞推迟。紧张关系至此终于公开化。波音在公开回复中表示,将与包括洛克达因在内的供应商合作,共同解决阀门的问题。这时外界清晰看到了:波音的举动相当于把供应商丢出来背锅。
后续的发展就愈发匪夷所思,原本被视为顶尖、专业的公司们一起搓出了一个漏洞百出的飞船。
今年5月6日,在落后了SpaceX接近4年后,Starliner计划进行首次载人测试发射。火箭立起后,工程师们注意到飞船出现氦气泄漏,但管理人员认为泄漏的严重程度不足以影响发射。而当NASA宇航员布奇·威尔莫尔(Butch Wilmore)和苏尼·威廉姆斯(Suni Williams)已经被绑在Starliner的座位上,他们终于发现飞船下的Atlas V火箭也出现压力调节阀故障。
两天后,美国最大的新闻稿发布平台美通社上出现了一篇稿件,长期为NASA供应阀门的航天供应商ValveTech以公开发稿的方式试图叫停发射:由于阀门泄漏表明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NASA应该立即叫停Starliner发射。
“作为NASA的合作伙伴和阀门专家,我们强烈建议他们不要尝试发射,风险还在发射台上。”ValveTech公司总裁Erin Faville说。
对所有相关方来说,一拖再拖的发射成了一块急需的遮羞布,只要一天没发射成功,新的问题就会一直出现。他们很需要一次成功来合上这本烂账。
资金的流动,人才的走向,构成了技术进步的基础动力,一步一步画出未来的科技图景。资金是政治和商业实体的意志体现,而最顶尖人才的选择往往有梦想为指引。
坐落在美国西北、与加拿大相望的港口城市西雅图,如今的光环少不了它作为微软和亚马逊的总部所在地,作为不同时代科技产业的代表,催生出了比尔·盖茨和贝索斯两任首富。
顺着科技史的脉络往前翻看这座梦想之地的历史,它还是波音的故乡,在上世纪50、60年代那个巨型工程改变世界的年代,受梦想感召的年轻人涌向西雅图。
从那时起,创造地球上最复杂的机器对工程师来说是绝对的诱惑。这也让波音长期位列美国年轻人最想去的公司之一。
“在这里工作的很多聪明人可以选择做别的事情来赚钱。但他们喜欢飞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学教授丹尼尔·黑斯廷斯(Daniel Hastings)说。“当一架飞机飞过时,他们都会抬头看。”在那个黄金年代,他们有最好的商业民航飞机业务,航天业务所属的波音防务部门则被认为是一个全球知名的军火商。
两架接近全新的737 MAX客机分别坠毁于印尼和埃塞俄比亚,牵扯出波音内部混乱的治理问题。叠加疫情的因素,波音的股价跳水至近年的低位。两次危机消耗了300亿美元的现金,并引发了自911事件以来最大的内部动荡,光是西雅图就有6000名机械师离开。
和记官网
佛罗里达理工学院奥尔德林太空研究所所长Andrew Aldrin说,他身边的工程系学生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将目光投向了马斯克和SpaceX。高管也是如此,曾经拍板了商业载人合同的NASA副局长威廉·H·格斯滕迈尔(William H. Gerstenmaier),在2020年加入SpaceX,后升为公司副总裁。
加入SpaceX的人往往受到理想主义的感召,不管是星际旅行还是拯救人类之类的科幻设想,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高达每天20个小时的艰苦工作。而与波音飞机工厂同城相望的亚马逊,也在不断挖角前者的工程师,这些前波音员工可以在不搬家的情况下,拿着大幅涨薪的offer加入亚马逊。
就业统计显示,SpaceX和蓝色起源为刚毕业的航天工程师开出了9.5万-11.5万美元的年薪。而波音和NASA给出的薪资范围约为上述数字的7折。
双重因素的影响下,NASA和波音继续失去对顶级人才的吸引力,新一代的年轻人在SpaceX和亚马逊、蓝色起源之类的公司里名利双收,不知疲倦。
他们在成为商业航天的明星的同时,也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工业创新。在新一轮的太空时代里,波音逐渐被挤出了舞台的中心。
图:2018年8月,NASA发布商业载人计划宇航员名单,将分别乘坐波音(左边5名)、SpaceX飞船(右边4名)前往空间站。丨来源:NASA
最后转身的是NASA。这个曾经和波音等军工复合体绑定在一起的保守官僚机构,在尝到了甜头之后也开始加速拥抱商业化。
带头改口的是现任NASA局长比尔·纳尔逊(Bill Nelson)。讽刺的是,这位上过太空的局长曾经被视为保守势力的代表。在担任参议员时期,他不仅极力反对商业载人计划,还主导了太空发射系统和猎户座计划。后者如今的成本已经超支8倍以上,研发投入超过200亿美元。而SpaceX在星舰上的研发加制造的费用仅有约50亿美元。
去年5月,比尔·纳尔逊在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面前就该机构的宇航员登月预算作证时,强烈支持与企业签订定价合同,并痛骂“成本+合同”是NASA的“瘟疫”。
在同一个时空,波音CEO戴夫·卡尔霍恩(DaveCalhoun)则表示,波音防务部门将停止接受定价合同(波音航天业务隶属该部门)。“我们有几个定价合同项目必须马上完成,以后再也不做了。”这位职业经理人出身的CEO,以整个波音的当下业绩和股价为基本立场。除了Starliner,波音在新型“空军一号”合同上也吃了大亏,让原本是稳定为波音印钱的防务部门陷入连年亏损。
太空并不是唯一的叙事,对波音来说,很明显这只是一个次要的业务。“我们未来将不会签署任何定价合同。”这种喊话是给分析师和投资者听的。相比之下,让华尔街相信他们更加关注利润才更重要。
当视线从Starliner身上离开,我们会看到波音防务部门逐渐回归到一个军火商形象,尤其是在冲突不断的当下,军用卫星项目和战斗机订单带来的利润还在填补Starliner项目带来的亏损。
从合同开始到现在,波音输掉了商业载人的竞赛,有起有落的故事来到了当下,Starliner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令人惊讶的是,波音居然最终造出了Starliner。”航天记者艾瑞克·伯格把这句话放在了文章标题里,充满了嘲讽意味。
波音已经逐渐抽身出这个曾经由它发力创建的赛道:人才流失,对应的是创造力停滞;NASA转型,带走了基本的资金支持和订单保证;拒绝定价合同,与SpaceX分道,更是在形式上拒绝了商业航天时代的当下范式。相比于载人首飞,这才是Starliner十年更重要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