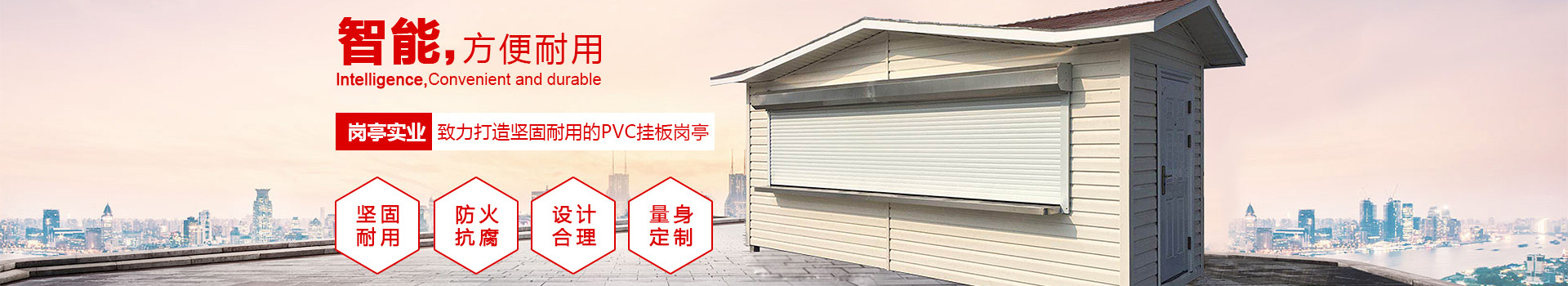我在《延川插队往事》一书所收延川北京知青邢仪的《那个陕北青年——路遥》一文中,发现了一则涉及路遥和林虹关系的新材料。当年,邢仪与林虹、林达同在关庄公社一个村子插队,相互比较熟悉,还与路遥后来的妻子林达是多年的好友。这是她比一般人更了解路遥与二林之间感情纠葛的原因。在路遥延川时期的感情经历中,林虹和林达先后是重要的当事人。路遥先与林虹恋爱,分手后,又与林达恋爱,数年后结婚生女,最后也感情破裂。路遥与二林的关系,虽然在他精神世界中不占关键位置,但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某种程度上,这是解读他作品中巧珍、黄亚萍和田晓霞等人物形象及性格特征的一个无法避免的参照。
目前的路遥传记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厚夫的《路遥传》、王刚的《路遥年谱》和张艳茜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等三部著作。他们在叙述路遥与林虹初恋风波时,持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林虹是北京八一中学初中生,1969年1月到延川关庄公社插队。她与路遥相识于县“思想文艺宣传队”,彼此萌生好感,逐渐发展成恋爱关系。1971年春,铜川二号信箱工厂(军工企业)来延川招工,路遥林虹都报名参加体检,林因身体不合格被刷下,结果,路遥出于炽热爱情,毅然把这个宝贵的招工名额让给心爱的女孩。林虹到铜川工厂后,也不负众望,将第一个月工资寄给路遥,第二个月,仅留下微薄的生活费,又用工资给他买了高档香烟等物品。几个月后,因分处异地和生活相差悬殊的关系,林虹对路遥的感情产生动摇,先是书信稀少,后向一位在内蒙古插队的女同学倾诉痛苦,这位女同学贸然代替林虹,给路遥写了一封绝交信。在这一过程中,林虹开始与工厂一个年轻的军代表萌生感情。刚刚被罢免县革委会副主任,又遭女友抛弃,路遥遭遇到平生以来最大的人生危机。最后,三部著作都把导致两人感情生变的原因,归结为林虹的移情别恋。
我查阅过相当一部分北京知青与路遥关系的书籍,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述。我推测这个“权威叙述”可能来自路遥本人,并借助好友曹谷溪、周海波的转述,成为目前这三部研究著作关于此事判断的主要依据。但它只是一个“孤证”,没有其他旁证予以证实。尤其缺乏林虹关庄公社插队知青提供的旁证,这就使它显得格外孤立。我认为路遥和林虹的关系,至今存在着两个悬疑问题:一是路遥主动把招工指标让给了林虹;二是由于两人生活悬殊较大,以及与军代表的恋爱,导致林虹决定与路遥分手。在这种情况下,林虹感情上抛弃路遥,就牵涉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道德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已在刊发于2019年第3期《当代文坛》的《一份沉埋的孤证与文学史结论——关于1971年春的路遥招工问题》一文中,有过初步探讨。这篇文章根据林虹最近在延川北京知青微信群里的一个微信,微信说:1971年春,铜川二号信箱工厂来延川招工,是要一名普通话较好的播音员。自己当时在县里就做过播音员,因此被录用,而路遥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口音,并不符合招工单位条件,所以,这个招工指标并非他的赠予。这个重要旁证一出来,就成为路遥原先那个孤证的参照性视野,虽然未必一下子就能推翻路遥的孤证,但至少也对它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一个问题,是说林虹主观上移情别恋才断绝与路遥关系,还其实另有原因。我将在下面继续讨论。
邢仪的《那个陕北知青——路遥》中的那份新材料证实:“L(指林虹)在队里待的时间最短,一年后她就被招工走了。听说L离开延川后很快和路遥断了恋爱关系,原因是遭到了L的家长的强烈反对,他们的恋爱关系夭折了。”
这是我见到的路遥和林虹关系第二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旁证。此前,关于它的原因只有路遥本人的孤证,以及三部路遥传记根据它的发挥和传播。首先,邢仪并未说这个招工指标是路遥出让。但究竟是不存在这个事实,还是她不知实情,目前不得而知。其次,林虹与路遥分手,“原因是遭到了L的家长的强烈反对”。这是一层客观因素。到底是父母反对在先,还是林的主观抛弃在后,或是她迫于家庭压力才做出这种决定?邢文并未明确叙述。
1970年代,其实不光是女知青家长,就连很多一起插队的女知青,也不看好北京女知青与当地青年(农民)建立恋爱关系。这是路遥和林虹关系之外北京知青和家长态度的“外部氛围”。它涉及城乡歧视、户籍关系、生活习惯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现实考虑,也包括习俗观念、子女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后来,看到好友林达和路遥谈恋爱,邢仪也在心里犯嘀咕,担忧女友能否真正预见他后来的成就和声誉:“刚开始我们这帮同学并不看好他们的恋爱,其实也没有明确的观点,只是觉得北京知青找当地青年,合适吗?”
我在这篇文章里还得知,反对自家女孩与陕北农村青年谈恋爱,并非林虹家长一例,大部分家长普遍持这种态度。随着路遥和林达关系的进展,林达家长从不理解到逐渐接受,林达也为取得父母支持,专程带路遥到北京禀见他们。邢仪与林达关系较近,比较了解她的性格,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她家长的态度,不过,行文中似乎有保留态度。“作为侨委干部,达的母亲比较开通,对于达与路遥的恋爱,她无奈地说:‘女儿爱上了,我有什么办法呢?’然后达妈妈要召见这位陕北女婿。达带着路遥回北京了,达还带着路遥去看望在北京的许多同学和同学的家长。家长们好奇地观察着随和的、收敛的、敦厚的、健壮的路遥,有的评价说,路遥长得像当时的体委主任王猛,比想象的好。(不知他们原先想象的是什么样子)又有的家长说了,这个陕北小伙子真不错,但如果是和我闺女,我不同意。”这则新材料进一步证实,L的家长反对态度,在北京女知青的家长中间,其实比较普遍。
女知青家长的担忧不是毫无理由,在遥远的陕北,就曾发生过几起这样的人生悲剧。
一个是在冯家坪公社彪家沟大队插队的北京女知青王援朝。当时,村里知青因招工和当兵纷纷离开,只剩下她一个人。孤独的她,慢慢与夫妻感情不睦、有三个娃的生产队长刘来生成为相好。王援朝是村里养猪姑娘,她见刘来生在妻子回娘家不归,一个大男人照顾三个孩子,便帮他洗一家人的衣服。和记app官网生病时,还陪着赤脚医生给他治病。一天深夜,刘来生来帮王援朝接生12只猪崽。“此时,两颗心紧紧地贴在一起,暴风骤雨地爱了一回。”后来,王援朝挺着大肚子回北京待产,被上过朝鲜战场的老革命父亲狠狠打了耳光,并把生产队长刘来生告到县里。1973年春,刘来生被判刑四年,“当刘来生被宣判的那天,王援朝肚子里的新生命嗷嗷啼哭着来到了人世间。”在内外压力下,倔强的王援朝执意不回北京,索性把自己铺盖搬到了刘家,与老人孩子过起了日子。“王援朝风里劈柴,雨中挑水,耕种锄割,滚碾推磨,打场缝补,伺候多病的老人,抚养孩子,一年365天。她完全没有了一个京城姑娘的模样。”“四年啊,煎熬的日子并不短暂。”刘出狱后,王援朝与他办了结婚手续。1986年,被安排到延川自来水厂工作。
另一个是王光美的亲戚汪鸽。她18岁到延川插队,知青嫌她是“最大资本派”的亲属,拒绝与她同组,女知青深夜12点,还把她的行李扔到了院子里。痛不欲生的汪鸽,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在刘家沟一棵槐树下哭至深夜。有一次,一条灰狼朝她扑来,多亏一条狗救了她。为生存下去,汪鸽无奈嫁给村里一个青年农民,生下女儿马延都,但夫妻毫无感情。婚姻维持不下去了,要离婚又离不了,“无奈之中,她给周恩来总理去了一封信,倾诉她不幸的婚姻。后来在陕西省委领导的督促下,当地政府主持她离了婚,被推荐上了延安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黄龙县的农村做了小学教员。”在这一过程中,她把女儿留在男方家,等于抛弃了亲生孩子。1987年,曹谷溪偶尔听说,当年汪鸽离开后,幼小的女儿跟奶奶过,奶奶病逝,十几岁的女孩经常穿着露肉的裤子,连学都没上过……曹谷溪出于同情,把这个女孩接到自己家,又费了很大劲找延安地区劳动局局长胡志清,特批了一个招工指标,把马延都安排到延川一家国营食堂当服务员。后来,他通过繁琐的关系,曲折地找到王光美家的电话,说明情况,终于联系到了在北京另外成家的汪鸽,使这对失散多年的母女重逢。“阔别20余载的汪鸽、马延都母女在北京相见了,喜泪悲泪一起洒在金水桥畔。”
两位女知青因为错爱,一个把自己留在陕北,一个把女儿抛弃那里。王援朝由于一时冲动,竟在彪家沟当了十几年农民,30几岁虽然到县城当了自来水厂工人,丈夫刘来生恐怕还是农民身份。当年的过失,一直在多年后发酵、延伸和变异;被母亲王鸽抛弃的马延都,则无辜沿袭了母亲不幸婚姻的痛苦,王鸽为之付出的代价,却要女儿一人独自承担。这就是说,26000多名北京知青插队陕北的运动结束了,可是由那场运动发展而来的“知青史”,还在王援朝、马延都,以及因各种缘由留在陕北的北京知青们身上发展着,并未结束。
实际上,北京知青家长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1971年后,全国各地农场和插队地区的管理人员,以及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借招工、当兵和上学等条件的诱惑,破坏知青运动的事件屡屡发生,震惊了大小城市的普通家庭,包括高层领导。为此,从中央到各省市下达各种,指示公安检察部门,严厉打击这种破坏知识青年上上下乡运动的罪恶行为。
据《青春履痕——北京知青大事记》一书统计,仅1970年,延安地区就发现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嫌疑人546人:“3月12日,延安地区办理打击破坏上山下乡案件26起,批斗11人,拘捕8人,其中判刑7人”;“7月12日,延安地区召开万人大会,公判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10罪犯”;9月,“全区共揭发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嫌疑人510名,判刑90人,其中死刑3人”。知青来陕北插队不到两年,就有这么高的发案率,现象实在惊人。因这本书不到10万字,且记录的仅是“大事”,没有对具体案件的跟进和详细描述。因此,我们不知道,这546个嫌疑人当中,究竟有多少与引诱伤害女知青有关?有多少是其他事件?但仅从这些“公判现象”看,足见当时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势的严峻程度。一年内,延安地区就发起三次打击破坏分子的大规模运动,以声势来震慑犯罪分子,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然而事件依然频发。通过插队延安的北京知青的大量书信,这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也会飞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令知青家长,尤其是女知青家长,为孩子插队的自身安全充满忧虑。
汪鸽的事情发生在这一期间,她不是出于爱情与当地青年结合,而是被迫结婚。王援朝的事情,应该发生在这以后,估计是1972年到1973年之间,因为,村里的知青大多数已经离开。阳波一篇访谈文章里有王援朝的内容,尽管采访对象说她“最幸福的是找了一个好男人”,笔者不相信当时她与刘来生的非法同居是完全出于爱情。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为找到安全感,大概是这位年轻冲动的北京女孩的优先选项。生产队长对村里最具权威的人,她不找普通农村青年,而冒着舆论风险找这个有妻室的男人,与安全考虑关系甚大。王当时就二十挂零,刘是生产队长,乃有夫之妇,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情商上大概比王成熟。作为接受、管理知青上山下乡的一方,无论何种理由都不应该给王援朝任何异性感觉,况且是在大多数知青都离开,她孤身一人生活在村里的情形下。而且他不可能不知道,当时延安地区对社、队基层干部侵害女知青行为所保持的严打和高压的态势。他是明知故犯,所以,王父气急打女儿两个耳光,又愤怒地向县里有关部分投诉刘来生的行为,实属情理之中。
由此可知,林虹家长强烈反对她与路遥的恋爱,强迫她切断两人关系,是出于保护女儿的考虑,并没什么过错。因此,这份材料不单是研究林路二人分手原因的新参照,对研究路遥与林达的爱恋、结婚到感情破裂,也不失为一个新面向。
然而,我的好奇在于,为什么三部路遥传记不约而同在“路遥和林虹分手”问题上,都将理解之同情偏向路遥了呢?我推测它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这则“林虹父母强烈反对”的新材料,出现在作者写作传记前后,他们无法在此期间及时地掌握了解。只能选择以路遥对曹谷溪单方面的“哭诉”为依据。这就容易把林虹内蒙古插队女同学代替她给路遥写绝交信的事实,以及林虹与铜川二号信箱工厂年轻军代表恋爱的后发性事情,不加分析地嫁接到“路遥哭诉”上,这无疑加强了林虹背信弃义的主观感彩。
二,在陕北传统风俗中,历来有在婚姻关系上强调男人颜面的习惯。三位传记著作的作者,有两位出自陕北的延安、榆林,因为主要利用的是曹谷溪关于路遥向他哭诉的叙述,鉴于不自觉的感情倾向,就会把路遥和林虹关系的内外原因,归咎于林虹的背叛。在我看来,当地传统风俗实际强化了林虹与路遥分手时的主观感情态度,不利于作者在叙述事情原委,分析各种原因时,保持客观和超然的叙事姿态。
三,由于当时北京知青,大多数人是因形势来陕北插队,所以心理上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历史巨变中的“过客”。我翻阅相关材料,发现在他们集体性的历史叙述中,谈论的多半是插队生活的艰苦、劳动之繁重,以及陕北老乡的厚道等内容。这跟他们只是来此走一遭,一遇招工、当兵和上学等返城机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的普遍心理,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关于知青与当地男女青年的恋爱婚姻轶事,除少数当事人,大多数人没兴趣讲述。无形之中,这就致使在诸多关于“插队回忆”的著作中,相关材料的匮乏。如此看,即使三部传记著作想做到不偏不倚,也无法采集到真正有用的材料。
最后,联系以上材料和分析,我想林虹之所以抛弃路遥,知青家长之所以强烈反对女儿与当地农村青年恋爱,是他们对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心存疑虑的表现。从1968年提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1979年启动“知青返城”政策,前后差不多有整整十年时间。一个人从十六七岁到二十六七岁,或是从十九二十岁到二十九三十岁,这中间完全错过了上大学、当工人、当干部等的时间窗口期。对一部漫长的历史来说,“十年”不过是一个瞬间,但对于大多数适龄青年来说,这却是最宝贵的岁月。
当年延川著名知青之一,担任过延川团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做公司高管的陶海粟著文反省说:“下乡之前,我们对农村的了解大多来自《朝阳沟》《李双双》等文艺作品,在那些作品里,农村是一片‘花好月圆’的‘艳阳天’。但我们眼中看到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很多地方,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处在一种近乎原始的状态。我们落户的第一年,所在生产队的社员们辛苦了大半年,夏收时每人只分了一升麦子。在学校里吃‘忆苦饭’觉得难以下咽,但在这里,那是很多人的家常便饭。”陶海粟的反省视角,把路遥和林虹关系放到了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这位当年的知青干部,没有像大多数知青那样简单抱怨历史,而是理性地认为:“固然,我们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者,当时并没有能力把握这些现象背后的理论上、制度上的原因,更没有能力把握这些现象,甚至理解那场贯穿20世纪的空前规模的人类社会实验运动的内在联系。但是,经过那九年的社会实践的再教育,培育了我们与普通老百姓的情感,塑造了我们的人格,为在适当的条件下拥抱新思想、新世界做了准备。”